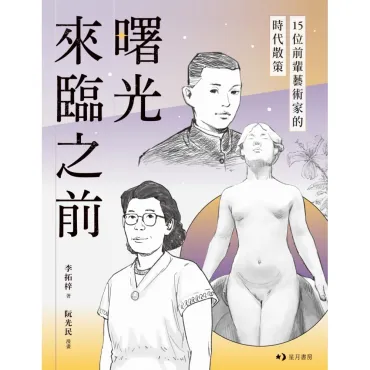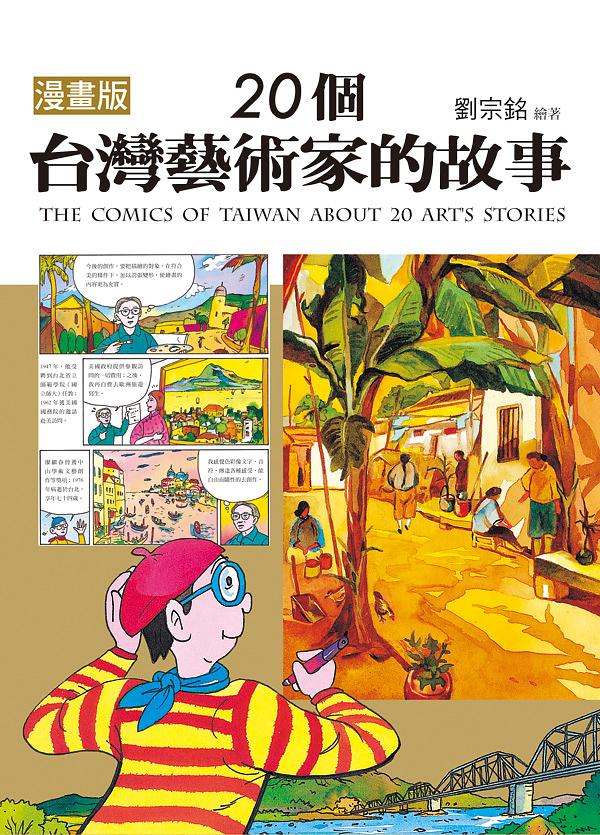她們知道自己是美的——陳進筆下女子的自信與靈光|《畫途中:臺灣第一位女畫家 陳進》王欣翮賞析
文/策展人 王欣翮
我初次接觸到陳進時還是位小學生,母親買了一整套的藝術家介紹書籍,從達文西一路漫談,最後一本的主角則是陳進。我翻閱著那本畫冊,陳進筆下的女子們個個容貌姣好,無論是身著旗袍、漢衫,手上興許握著扇子、月琴或是笛子,都看起來自在光彩,自此我就被她筆下那些摩登的女子們迷住。
在《畫途中:臺灣第一位女畫家 陳進》,作者鄭若珣與繪者張梓鈞,便巧妙地將這些閃閃發光的女子們呈現出來。
陳進,1907年出身於新竹香山的望族,為家中三女。1922年,她入學臺北第三高女,在鄉原古統的指導下開始學習日本畫,並在日後赴東京留學。她曾多次入選「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更在日後成為第一位以東洋畫入選日本與其殖民地最高殿堂的帝國美術展覽會(帝展)的臺灣人,實為當時女性的榮耀。其繪畫主題泛及人物、花卉與風景,而最受歡迎的莫過於她以臺灣女性為主角的繪畫。
這本繪本從一趟未知的旅程作為起始。在櫻花搖曳車站下踏上路途的實為陳進本人,她儘管對未來不甚確定卻又姿態果斷,路途上與其相遇和同車的乘客,無一不是陳進繪畫中的各種女子。她們以旅伴的身分親暱談笑,從其姿態和配件中能清晰辨認出每一位的風貌:如〈含笑花〉身著藍色旗袍與光澤絲襪摘花的女子,以及一旁的短髮紅衫少孩;或是拿著笛與月琴的永恆少女搭擋〈合奏〉,而亮黃色漢衫綴有藍色飾帶的女子則出身於〈化粧〉,還有始終橫躺著手握《詩韻合璧》閱讀的旗袍女子,則來自於其代表作〈悠閒〉。這一系列幾乎都是1930年代,陳進以姊姊陳新與其友人為模特兒的作品。
陳進嫻熟日本畫的技法,並以此繪製出我們難以窺見的臺灣上流女子生活,在原畫中這些女子不僅身著華服,還總是處在黑漆螺鈿鑲嵌的家具之間,然而這些家具難以在公車這個場景裡表達,於是繪者張梓鈞將重點留在了女子們的衣著身上,特別是首飾和服裝的細節。若有機會實際看陳進的原畫,便會發現她對於這些細節的質感著力甚深,她會先勾勒出輪廓後,再用顏料反覆堆疊厚度,讓顏料浮凸在絹或紙的表面,甚至貼上金箔或銀箔增強,這些質感細節成為陳進筆下的大家閨秀們如此逼真完整的原因,也成為觀看陳進作品時的小樂趣,而這些細節被再次轉化並呈現在繪本之中。
旅伴亦納入陳進曾任教的屏東女高。陳進在1934年時赴屏東任教三年,期間她的目光從大家閨秀轉向於田野間的排灣族女子。繪本中多次出現的排灣族女子們,即出自現在典藏於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的〈三地門社之女〉,部落女子身著素衣,充分吸收陽光的膚色健康閃耀,背景簡練不若以往華麗,但是女子們逼人的氣勢,明明是生活場景卻又若在商量著部落大事。
陳進畫中的女子呈現出畫家理想的美,這份美時而節制秀氣(如〈合奏〉),時而氣勢逼人,特別是在排灣族女子和〈悠閒〉與〈化粧〉等作。她們呈現出一派飛揚自信,視線沒有直視觀眾,卻又將自我生活大方地展露給了繪畫外的觀眾,宛若他們才是主宰這幅畫的本體,並非只是賞玩的觀眾,這形成了陳進筆下女子永恆的魅力。她們完全知道自己是美的,更享受著自己的美。
繪本亦提及了幾個陳進生命的重要轉折,如戰爭期住在東京的生活苦難,以及戰後回到臺灣面對延燒多年的「正統國畫論爭」(起於外省畫家批評臺灣畫為「日本畫」,實為民族本位與傳統現代之間的角力),後者直到1977年林之助提出以「膠彩畫」為這種作畫方式命名,方才落幕。這些事件在陳進的生命中不可能輕鬆,繪本以突如其來的驟雨與飛機表達了這段時期的震盪,特別是藝術家遭受論爭波折時,無論是其繪畫題材或是表現方法都曾被各種質疑,逼得她一度開始學習中國筆墨技巧。
在外在的混亂下,陳進在四十四歲迎來獨子蕭成家,她的重心也轉向了家庭。這不代表陳進不再繪畫,而是她將重心移至與家人相處的時光,記錄下了許多多幅母與子,或者逐漸成長的小孩圖像,從日益溫暖的筆觸和用色,能感受到畫家內心從中得到的平靜。
繪本收束在佛像。當所有話語都落盡,如花般女子們走進畫室,看著陳進伏在地上,緩緩描摹著觀音像。屋裡香花繚繞,日本畫的修習使陳進特別擅長畫花,而這些花也成為她作品中的特色。最後一幕,陳進筆下的觀音像面容慈悲祥和,墜飾細節如同她多年來細膩描繪的女子們般華麗,但那觀世音略垂的眉目、頸子幾道橫紋,都顯露出那歲月積累下的智慧,也讓觀世音多帶了份親切。
觀音好似看盡風華的陳進,祥和地面對世間。